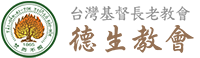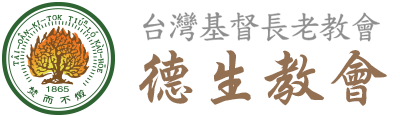1
我毋知影妻是按怎會去買彼隻鳥仔轉來,伊講:「佇夜市仔看著,感覺伊可憐,就給買轉來矣。」我給斟酌看,是白耳畫眉。鳥仔予妻囥佇房間頭前的陽台,一透早,唉就假若有心理病仝款,啾啾叫,叫袂煞,佇籠仔內khok-khok跳懸跳低,害我倒佇眠床頂嘛聽甲無張持緊張神經質起來。我給妻講:「妳敢會使叫彼隻有病的白耳仔莫閣khok-khok跳矣?若無,規氣給放放出去。」妻應講:「啊就是按呢毋才看伊可憐的嘛!閣再講,按呢的鳥仔給放出去,嘛乾焦是揣無吃、飫死一條路爾敢毋是?」妻真堅持,我只好繼續接受伊佮鳥仔精神上的苦毒。
閣較害的是我自來毋bat想過,我一日透早會因為醫學的特殊理由佮妻鬥陣。伊量體溫,判斷彼日是「排卵期」,就要我請假佮伊去婦產科做檢查,尚重要的是,佇檢查晉前,夭壽骨阮閣必須要先合房[kap-pâng]。彼个檢查有一个奇怪的名叫做「性交後試驗」。佇按呢的早起無閒彼項予我感覺真無神,見若毋是位感情的角度出發的,哼我認為它就屬佇獸類的層次。好笑的是規个過程平波波無起無落,袂輸一个唐突恬靜的儀式,一直到結束,我遂完全無臭無汗(毋就假若一隻狗?)事後妻恬tsuh-tsuh倒值床頂袂振袂動,伊講,是醫生交待的。「這是牢[tiâu]胎的姿勢,要維持半點鐘。」伊的聲調內面有一款莊嚴的母性的氣氛,予我笑出來。伊看我嘻嘻哈哈,就受氣矣,頭斡過來講:「敢講這件代誌你無責任?閣有,尚急欲抱孫的人敢毋是恁老爸?」
這站,親像按呢的情形已經無特別。拄結婚的時,因為猶未生子,我佮妻確實享受過一段清閒自在的日子,上山落海,嘛做伙去過幾落个國家蹉跎;毋拘,當阮想起要有囡仔的時,這个清閒遂就成做壓力矣。阮一直無法度有囡仔。沓沓仔[ta̍uh-ta̍uh-á],阮鬥陣的時所想的全是這个任務,這予人真厭僐無神。妻認為一定是佇伊或者是我成長的過程中,有啥物無發現的罪,所以伊的腹肚才會到旦無動靜。所以,伊堅持要揣出彼个罪。這馬,「罪」的想法含[kânn]佇阮中央,已經成做一粒我心肝頭的臭膿。我毋知影按呢的看法位佗來的,毋過,我按算拒絕它。哼哼,自古來,宰人放火的惡人定定是子孫仔滿堂敢毋是?
病院診間的壁頂頭掛一幅白鸛[kuàn]展翅的圖。晉前佇我佮妻的房間壁的頂頭,嘛bat掛過仝款的一幅,是妻特別揣真久才買著的。北歐的人講囡仔攏是白鸛用嘴咬咧送來的,所以,給白鸛叫做送子鳥。妻認為掛彼幅圖會予伊好運(若論罪,這个迷信的想法咁會使脫罪?)彼幅圖內面的鸛翅鼓展開,白色羽毛的外圍是一緣烏色的毛,佇日頭下,確實假若有一个白布巾包起來的紅嬰仔予牠抱佇胸坎,我愈看愈綿精1。「你敢會留佇遮?」妻欲做內診的時,護士小姐問我。我搖頭。目睭金金看另外一个查甫人給傢俬囥入妻的身體,閣按怎講我嘛無法度慣習。「按呢,請先口面2等。等一下會閣請你入來。」護士小姐假若知影我的礙謔[ngāi-gio̍h],用一个同情的聲調講。我就佇候診室等。安徒生bat寫過一篇白鸛的故事,內面講有一群狗怪囡仔唱歪歌恥笑當底學飛的白鸛的鳥仔子,路尾手,彼群白鸛學會曉飛了後,真袂爽,就給一群死去的囡仔送予遐狗怪囝仔做小弟小妹──我給妻講這个故事,奇怪,伊聽了真無歡喜,認為我故意講歹聽話予聽。
尾手過無二日,伊就給彼幅圖位壁頂提落來。這馬想來,妻所講的罪,嘛毋是完全無道理。我敢是彼群恥笑白鸛的囡仔的其中一个?
這个想法沓沓仔佇我的心內茁穎[puh-ínn]:我知影,佇表面的「我」下面,恐驚有另外一个「我」,阿彼个「我」的想法閣是hiah呢汰膏垃圾,完全是表面的「我」無法度承認的!
「先生,請入來。」護士小姐叫我。
妻已經peh起來坐佇椅仔頂,掛金框目鏡的醫生一直看電腦螢幕:「佇拄才的檢查,太太的子宮頸發現有12隻精蟲,這表示精蟲的數量、活動力閣有對子宮頸黏液的穿透力正常無問題。一般來講,子宮頸黏液是精蟲向前泅最大的阻礙,有通過12隻已經是袂bai2。」這表示啥物,我想無,醫生嘛講袂清楚,總講一句,伊給阮恭喜,因為阮猶閣真有機會有囡仔,毋過要繼續打拚。毋知是安怎,我真討厭看彼个醫生的面。行出診間我挑故意假笑魁:「我甘願給神求嘛無相信這个醫生的話。」妻就給我凝:「哼!你的信心敢袂傷大?」伊焦笑二聲。我雄雄發現這已經毋是我所熟悉的彼个妻(老實講,位阮想欲生子,我就毋bat聽過伊笑),聲調內面,有我無法度瞭解的不滿。
2
暗暝,阮社頭仔迎鬧熱,阮爸自幾日前一直堅持我要去吃辦桌,因為是地方難得的神農大帝刈香,幾年一擺。印象中這款代誌是阮阿公的穡頭,阮爸一向是激外外毋bat底睬的,毋過,阮阿公二年前過身去矣,這遍阮爸遂變做阮林家的大家長,雄雄熱心甲。阮爸的意思假若講這是伊的面子,所以,我一表示我尚好莫吃拜拜的時,伊就激面腔予我看,真有欲斷絕爸子關係的範勢3,這予我真不安。我認為我的老爸並無顧慮我的想法,因為我的丈人規家是基督徒,閣再講我為著娶妻,表面上嘛勉強洗禮矣,這馬閣是佇阮丈人的建設公司吃頭路,我相信阮爸的堅持乾焦會造成我的不幸爾爾。
「好啦,恁尪仔某掣[tshuā]來孝孤就著啦。恁契爸火樹叔公嘛八十外仔外矣啦,這回的香刈了,敢猶閣有後一回就毋知矣啦!」阮母仔按呢嚅[nauh]:「無,嘛看佇恁契爸仔的面子,伊外疼你咧!」
我的契爸火樹叔公,是六七十冬前神農大帝揀選的老乩童,我細漢歹io飼,阮母仔就給我契予伊做子,逐冬過年初二的查某子日攏要轉去怹兜吃飯吃到16歲,彼是阮hia的例。Hín時我的頭殼熠過一个畫面,是幾年前火樹叔公去到阮兜園仔做客的情景,阮欲種一欉桂花,伊提圓鍬鬥相工翻土,是幾十年專業的老農夫的正範[pān]的屈勢。日頭照佇伊規面的汗頂頭,予人一款特別深的年歲的印象。
拄才阮母仔講話的口氣有淡薄仔稀微。我問阮母仔:「誰知影神農大帝是誰?恁拜的是誰恁敢知?」我就聽見伊「唉!」吐一个大氣。
伊講:「唉,譀譀[hàm]矣啦!」
哼哼,這款鬼神的代誌,這馬我是真無想欲信斗的。
怹一隊人馬天未光就出門,去到屏東的海墘仔刈香,閣倒轉來到社頭已經是下晡三四點,挵鼓挵鑼,鬧熱彩彩,假若欲給規个社頭囂[hiau]過來的款。我無倚過,是到暗頭仔怹給桌擺出來,
我才佮妻勉強到位坐桌吃飯。
妻僐僐講:「若是阮爸知影,定著無歡喜的。」
「毋是逐項攏要予知嘛。」我按呢應。
彼桌菜是袂歹吃,嘸過阮坐傷頭前,卡拉OK康樂隊的歌聲予阮真歹消化。我略仔算,全部擺三四十塊桌坐滿滿,規个社頭的人攏來到位。姓吳的、姓林的、姓簡的、姓李的,我自從退伍回鄉到旦,毋bat看著這呢濟鄉親坐做伙,阿恐怖的是,假若每一个面我攏熟悉熟悉,毋過遂喝袂出名。其中我感覺有幾个少年家仔特別面熟,問阮母仔,伊講:「遮少年輩的,我嘛bat無二个啊!」按呢二三擺,我就無閣問矣。桌擺佇阮社頭的下路,是我做囡仔走闖的所在,桌邊拄好是彼欉阮時常佇樹下蹉跎的檨仔樹,阿佇彼條下路,阮嘛時常踢銅管仔,銅管仔飛出去的乒乒乓乓的聲那像閣真明,毋過,我給頭斡來斡去,按怎都認無一个囡仔伴。我雄雄發覺家己是故鄉的外地客。
「你看彼康樂隊,敢講恁地方的人攏是遮呢無聊的?」妻講。
我無應伊。
阮爸佮我的阿叔一直叫我上台唱歌,真心適,怹攏講愛聽我唱歌,我一直應好,毋過一直無唱。台頂的彼个查某主持人自稱阿美,妝畫真厚,穿紗仔衫,低俗裸露,對每一个上台唱歌的人攏會司奶二句,閣給伊的胸仔貼佇怹的身軀khok-khok-kô;無三二下手,我的雞母皮已經交落[kau-la̍uh]規土腳。我閣詳細看,he是最近真時行的貨車所改裝的流動舞台,是給貨車後斗的車廂四面展開所成做的金光熠熠、鬧熱扠扠的舞台。舞台頂較倚後面的部位徛一塊看板寫「音美歌舞團」,看板的頂頭貼一張紅紙,寫:「恭賀神農大帝刈香繞境大典闔家平安」,看板的後面坐一个彈電子琴的琴師。阿美仔差不多三十外歲欲倚四十,穿一軀粉色有真濟水晶珠的比基尼式的服裝,懸踏鞋真懸,見若人唱歌,伊就伴舞,二个奶仔佇懸懸的台頂動動晃;特別若是歐里桑,伊就將胸仔貼佇怹的身驅lù懸lù低,閣手牽手跳舞。「夭壽喔,去佗揣來這个妖精?」台仔腳的歐巴桑嘛笑加咬咬叫,就算台頂佮妖精跳舞的是怹的老伴,嘛假若無要無緊的款。哼哼,誠實是嬈記記無正經的歌舞暗暝矣……我想欲將目睭徙開,毋過真無法度,我的目神不時貼佇彼个主持人阿美仔的胸坎……
就佇這个時陣,我的手機仔喨[liang]起來,偃頭一看,是我無熟悉的電話號碼,我給切斷,結果它過一下仔閣喨,我切斷,閣喨,按呢二三擺,我就給接起來。想袂到,電話的彼頭是一个查某囡仔的聲,我感覺毋著,緊離開座位,行去較無人的所在。
「請問敢是Arthur?」
「按怎?」
「有一件代誌…我想欲當面給你…唉呀…咱敢會使見一个面?」伊的聲音聽著真秘四,假若底哭,小可稀微悲傷。
「小姐,等一下。妳是誰,我敢bat妳?」
「敢講,你袂記矣?我是,曾麗雲啊。」
「曾麗雲……曾麗雲……啊,我想起來矣,是妳!」是較早佇七迌場所熟悉的一个查某囡仔。
伊講:「我這馬佇會場呢!我拄才有看著你。」
「哦?」我驚一趒,四界相一下,看無伊的影跡。
伊繼續講:「我是來鬥相工辦桌的啦。」
我沓沓仔想起伊的面,佮伊這馬秘四的聲合[kap]做伙,雄雄抱心起來……彼是一个無真醒目,某一方面來講,是傷過膨皮大箍的面……閣再講,伊的哭聲真歹吉兆,若會使選擇,我甘願予人倒會仔嘛無要啥物代誌佮伊有關係!
伊本底隨欲佮我見面,毋過我講無方便,所以給拒絕。事實上,我無想欲閣睬伊,只是伊佇電話中苦苦哀求,我驚伊亂,所以勉強佮伊約一个時間地點,了後,隨就給電話掛掉。
行轉去座位,妻問我電話誰敲的,我烏白講一个同事的名,毋過,位妻僥疑的眼神裡,我隨就真後悔我所講的白賊。
暗暝佇眠床頂,我夢見彼个叫做阿美的主持人。我實在毋知影伊按怎看上我的,佇夢中,主持人行落舞台,來到我的身邊,完全毋管我的妻抗議,給我揪上台。我只好唱一條洪一鋒的〈放浪人生〉交差,彼是阮社頭的人攏甲意的歌。我聽見台下的噗仔聲,毋過看袂著阮厝裡的人,包括妻。佇我唱歌的時,主持人阿美仔為我伴舞,然後,伊牽我的手跳舞,閣將身軀貼佇我的身軀。最後伊的二粒親像雞規的大奶仔絚絚貼佇我的胸坎,柔閣軟、燒落燒落,我一下手感覺強欲袂喘氣,唱袂出聲。我的頭殼雄雄親像入魔公,一偃頭,發現阿美仔的面遂變做曾麗雲的膨皮面,續落,閣變做妻的面。
四箍輪轉一下手攏暗落來,親像烏暗的一片樹林。我緊闖落台,遂看見一隻灼火的虎位樹林內面行出來,恬恬徛佇我的面頭前,牠的目神是燒燙燙的火箭耀[tshiō]過來……
我喝一聲就醒來,半暝矣,彼隻白耳仔竟然閣佇陽台跳懸跳低……
1 綿精 mî-tsinn,專注沈迷。
2 口面,外面也。
3 範勢pān-sè,態勢。
~未完待續~
編按:本文是以文學的角度出發。作者胡長松兄係本會傑出的年輕作家,任職於電信
公司,曾任《台灣e文藝》、《台文戰線》總編輯與台文筆會秘書長,著有多本
台語小說與詩集,曾得過2008 年 台灣文學獎台語小說創作金典獎、王世勛
文學新人獎小說首獎、海翁台語文學獎小說類 正獎等,得獎無數。此外,長松兄
還對於台灣人長期被殖民的歷史和困境,以及台灣平埔族的演變,有著深入的
研究。